正午的话:
这篇稿子写于2009年初,没发表成。现在,七年过去了,冉云飞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更重要的是,新的社交网络已经替代了博客,冉云飞的阵地也已转移。我们选这篇文章时,自问是不是过时了?说实话,我们也不知道。
正午 谢丁

时代的病人
文/谢丁
一
1921年2月底,吴虞终于等来了北京大学的聘书。北大开出的条件颇为丰厚,直接以教授聘任,月薪260元。通常到北大当教员,一般须试讲一年左右,没什么问题,才能升为教授。吴虞算是一个特例,这全靠他在《新青年》上打响的名声。
此前四年,吴虞在《新青年》发表了一系列攻击孔家店的文章。这本杂志由陈独秀创办于1915年,是当时中国攻击儒家总体价值体系的标杆。吴虞以《吃人与礼教》一文成名。在新青年同人中,他和陈独秀二人,非孔非儒最为有力。
那年,陈独秀已将《新青年》搬回上海,编辑同人之间开始分化,杂志已近分崩离析。但远在成都的吴虞,正力求早日前往北京。他的堂弟吴君毅,写信对他说,北京才是人才荟萃之地,怀才抱器之士,来此间不愁无用武之地。如果留在四川,徒遭白眼,永无出头之日。
吴虞正急欲脱离成都的现实困境。因反对儒家思想体系,他已经被成都主流教育界围剿封锁。长达八年,吴虞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,没有任何一家教育机构敢聘请他。他写的文章,四川媒体也从来不登。虽然此时吴虞在外界已获得盛名,但成都的死水还是让他快憋不过气来。而在北京──全国文化运动中心,那里的新文化运动骨干们,都是吴虞非孔非儒观点的支持者。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,北京都将给吴虞带来自由。
多年来,吴虞和北京《新青年》同人之间只有神交。他和陈独秀通过几次信,所投稿件大多也有陈独秀编发。但他最欣赏的是胡适。1920年,吴虞的女儿因为出国留学,胡适做了担保,他才第一次提笔写信给胡适,表示感谢。
直到半年后胡适才回信一封,说“我是很敬重先生的奋斗精神的,年来所以不曾通一信、寄一字者,正因为我们本是神交,不必拘泥形迹。”同时,胡适也表达了他对吴虞在成都境况的支援:“先生廿年来日与恶社会宣战,恶社会现在借刀报复,自是意中之事。但此乃我们必不可免的牺牲——我们若怕社会的报复,决不来干这种与社会宣战的事了”。”
但成都的氛围远比北京更为保守。吴虞不仅在言论上攻击孔儒,他还因财产纠葛,一纸诉状将父亲告上法院。这引起卫道士群起攻之,将吴虞视为成都的污点。而吴虞是一个很在乎外界评价的人,他在成都没有丝毫满足感。
只有通过阅读外界报刊,吴虞才能从精神上寻找到支撑。在成都,“华阳书报流通处”是他和外界沟通交流的重要支点。那时,书报流通处刚刚兴起,读者可以在这里买到全国各地的刊物,从而摆脱因交通不畅和信息不通带来的封闭。从北京辗转而来的新文化力量,通过书报流通处传递到吴虞手中。他在这里第一次看到《新青年》,并萌生投稿的意愿。
拿到北大聘书后,在等待北大汇来路费的同时,吴虞到华阳书报流通处买了一本《北大纪念册》,此为北大自印,流传至成都。但凡与北大有关之事,吴虞都有留心。他阅读《蔡孑民言行录》,还向周围的朋友打听北大是非。他高兴的,小心翼翼的,做好一切北上准备。
吴虞能到北大教书,主要是他堂弟牵线,最终由中文系(国文部)主任马幼渔定下此事。堂弟来信告诫说,“北大党派复杂,初到此间,若不悉其内容,恐动辄得咎”。1921年4月6日,吴虞从成都出发,在重庆停歇数日,最终于5月7日清晨抵达北京。
当天,他和堂弟一起到中央公园来今雨轩看牡丹,约见马幼渔、马寅初、蒋梦麟喝茶。在日记里,吴虞如此描述他在北京的第一天:“幼渔、梦麟意见极反,而外面周旋,仍丝毫不露,足见江浙人之有心也。”
这一年,吴虞49岁。除了比蔡元培小5岁,他比《新青年》同人都年长。在四川长期受压抑的心态,导致吴虞察人观事,都持怀疑态度。在公共场合,吴虞尽量谨小慎微。但在日记里,吴虞记录了他周围所有人的“丑事”。和他交往的人,几乎都被他在日记里攻击过。而对于他自己,日记里满满当当,都是别人的赞誉之语。
离开成都时,吴虞或曾期待北京能带给他个人声望的增长,或许学问也可有精进。但在北大四年,吴虞成就稀疏。他仅有的声望,仍局限于之前批孔批儒的文章。脱离了成都保守派的土壤,他激进猛烈的批判仿佛失去了对象。
在北京,吴虞再也没写出哪怕一篇名噪一时的文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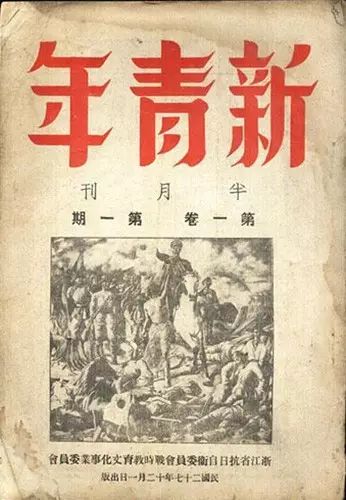
二
吴虞的日记出版,已是60年后,1984年。那时冉云飞还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念大二。多年后,他读《吴虞日记》不下十遍,写成《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》一书。吴虞不会想到,他一生无真正朋友,而在他死去半个世纪后,另一个居住在成都的知识分子,成为最了解他的人。
冉云飞对吴虞的情感也经历了波折。他本来是想向这个“老英雄”(胡适语)学习,向他看齐。但翻阅日记后,他却发现吴虞身上有许多不可捉摸的东西。在自序里,冉云飞写道:
“我发觉他既是中国社会的病人,也是中国社会之病的参与者、清理者、治疗者。他既勇又懦,既狡又直,既世故又不乏孩子气,既好名利又喜读书。他是一种古怪的结合体。这种古怪的结合,仿佛中国古堡里突然搜出了一份西洋地图,让你产生不配合的晕眩感。这种错位,让我感到困惑迷惘,不知所措,难以切入,但这更加激起了我对他的兴趣。”
冉云飞是四川某杂志的编辑,但他更大的知名度来源于网络。他分散在各个网站的博客,浏览量排名前三。冉云飞的文章,大多针砭时弊,倡导民主和自由。
冉云飞认为,在一个把传统连根拔起的时代,我们需要尽量理性地研究过去,以对当下有较为稳定的观照。对于他所期待中国发生的改变,他希望自己是“日拱一卒,不期速成”。
每天早晨6点,冉云飞起床上网,阅读新闻,并撰写评论更新博客。上午他会去编辑部上班。午睡过后,他开始阅读书籍直至夜晚。在撰写吴虞一书时,冉云飞游走在历史和现实之间。早晨是他面对中国现实的时刻,夜晚他将回到历史中。
某种程度上,冉云飞提倡的民主自由,和五四时期《新青年》同人倡导的德先生、赛先生,有异曲同工之处。但冉云飞认为吴虞那一代人激进得多。如今已很少有人再用激烈的方式去攻击儒家传统价值体系。现在,激烈的中国人仍然存在,但他们愤怒的对象不是孔子,而是任何伤害到中华民族感情的人。但在二十世纪初,对于《新青年》众知识分子来说,非激烈不足以救中国。
自晚清以来,中国人一直在尝试现代化的道路。起初,人们想通过“船尖炮利”的改造挽救颓势。后来,康梁兴起制度变革。但他们都没有成功。由传统读书人转变而来的现代知识分子,开始把目光锁定在中国的文化上。他们认为只有从文化上进行革新,才能从根本上救中国。
陈独秀认为,儒家价值体系势难与西方思想兼容并蓄,糅合为一。他在1916年写道:“求适今世之生存,则根本问题,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。所谓平等人权之信仰,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,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,猛勇之决心;否则不塞不流,不止不行!”
而此时,康有为却主张以儒家思想作国家宗教,他认为传统儒家思想可以提振国力,填补眼前生活令人触目惊心的道德真空。因此,以《新青年》为首的新文化阵地,对儒家思想体系的攻击也越发激昂。
吴虞搭上了这趟文化革新的快车。在成都,书报流通处的热卖,使他意识到媒体的力量。在新式学堂受教育,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城市阅读人口,是新式观念的可能接受者。吴虞将自己的《辛亥杂诗九十六首》投给《甲寅》杂志,由陈独秀编发。随后一发不可收拾,诸多文章发表在《新青年》上。
在《吃人与礼教》一文中,吴虞受到鲁迅《狂人日记》的启发,称赞到:“这日记,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,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,都被他把黑幕揭穿了!”他还指出,“我们中国人,最妙的是一面会吃人,一面又能够讲礼教。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,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,却认为是并行不悖的,这真是奇怪了!”
此时的吴虞仿佛一个斗士。胡适在北大第一次见他时说,“这人是十年前的激烈分子,在成都不为人所容。”在外界看来,吴虞和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有着共同的目标。但冉云飞却说,吴虞走得没那么远。他之所以激烈的非孔非儒,源自其自身经历,这是他求得内心平衡的一个重要方式。
在吴虞日记里,冉云飞发现了另外一个吴虞。
“他与时代并不合拍,与父亲不共戴天,和家人冷漠客套,与朋友几乎无真交心者,日记里记下了许多朋友阴暗的生活。进入他日记里的名人,几乎都有不堪的记录,这太令我意外了,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读到过一部像他这样的日记。你可以厌恶一个人,但吴虞好像与所有人暗中干上了,因为他几乎没有可以相信的人。”
冉云飞选择进入吴虞的世界,是他对那个时代的氛围有一种天生的敏感。他认为,现在的知识分子,正遭遇一些相同的困境。虽然早已没有外国列强入侵,但对于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追求,对普世价值的追求,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。
“我们现在面临的冲突是,你作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,你怎么去把握这种平衡?你既要让政府感受到,这个社会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好;你也要让老百姓感受到,这个社会也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糟。”
冉云飞最后写道:“我们每个人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制约,其间的不自在与求生的分裂,令人如此抓狂,只不过许多人的形迹没有记录下来罢了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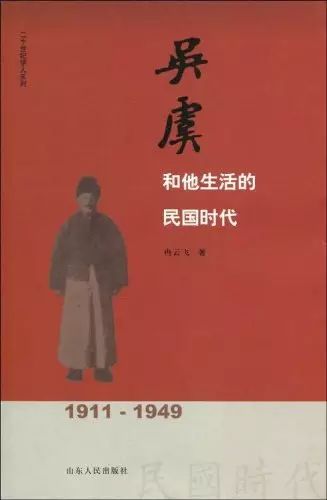
三
现存《吴虞日记》,以1911年9月10日开记录。一个月后,他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自己的父亲,称为“魔鬼”。吴虞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,影响他一生为人处事。
吴虞是独子,1872年生于成都。家境还算殷实。父亲以副榜贡生,曾任富顺县教谕。 在成都时,他就读于尊经学院,是吴芝英的学生。那时师辈们也夸他有才,算同学中出众之人。但他父母的关系一直不太好。母亲抑郁而终时,父亲续玄,把他赶回新繁乡下祖居,靠几亩薄田为生。这年他20岁,自此和父亲结下仇恨。
随着迁往乡下,学业中断。更可怕的是,吴虞唯一的儿子在新繁乡下因医疗条件简陋,医治无效死去。这笔帐,他日后也算到了父亲的头上。
1905年,吴虞和他的堂弟吴君毅,一起前往日本留学。他读了一个类似速成班的法政学堂,在那里并没有学到太多的东西,但却染了一点革命气息回来。回到成都后,留学背景让他很容易找到教职。但父亲却在此时向他索要赡养费。
那一点激进的革命气息,随之扩大。吴虞将父亲告上法庭。不仅如此,他还将父子诉讼的过程,和他认为的实情,写成《家庭苦趣》,广为散发,最后闹上报纸。几番折腾,一个家庭事件演变成一个公共事件。
吴虞之前有关非孔非儒的观念,本已让成都的卫道士们含恨在心,如今更是容不下他。虽然最后法院判决吴虞胜诉,但固有的父子观念和伦理秩序,已经被他打破。他受到成都教育界和新闻界的共同排挤。几个守旧派的死对头一直想把他挤出四川。
在成都,整个社会几乎都站在吴虞的对立面。不仅文化名流与他保持距离,平头老百姓也经常写信骂他。还有陌生人在城门旁边写文章驳斥吴虞。
冉云飞说,如果他的观念只是惹恼了几个头面人物,而民众实际早已视此为无物,那么当你身在其间,你不仅没有一种包围感,你甚至可能成为民众眼中反对社会积习的“英雄”。
但这种“英雄”的感觉,吴虞在成都是找不到的。那几年他备受煎熬。一些朋友开始疏远他,即便同情他者,往来也很少。在1912至1918年,吴虞处于孤寂状态。但这恰好给了他安静读书写作的机会,也更坚定了他反对儒家传统的决绝姿态。
此时,《新青年》和《甲寅》等杂志在成都热销。吴虞注意到,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发生新的思想革命。1916年12月,吴虞给陈独秀写了第一封信。他提及他排孔非儒之思想,以及其思想来源(列举了他所读古今中外的书),同时告知陈独秀,他手中还有《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》等文章。吴虞努力在寻找思想上的同道。
陈独秀很快回信,对吴虞赞誉有加。这一次书信往来,被陈独秀刊于《新青年》二卷五号的读者来信栏目。吴虞大喜之余,开始自费订阅新青年,并陆续寄去他所有稿件。这些文章在成都很难发表,却在《新青年》连续快速的登出。又因为其全国影响力,吴虞迅速积累了名声。他在日记里说,“余之非儒及攻家族制两种学说,今得播于天下,私愿甚慰矣。”他还自比英国人卡莱尔,说“文人亦英雄之一种。”自此,吴虞终于在成都之外,找到了“英雄”的感觉。
几年后,当《吴虞文录》在胡适帮助下得以出版时,亚东图书馆在广告里说:“吴虞是一个攻击孔教最有力的健将。卷首有胡适之先生序。”在这篇序言里,胡适评价吴虞为“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”,“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”。这两个标签伴随吴虞一生,成为他特殊的标识。
胡适也因此成为吴虞平生最钦佩的人。他一直追看胡适的著作,胡适推荐的书目,也一一找来读。多年后,他回到成都,出了《文续录》,还是首先想到胡适,把书送去。对吴虞来说,小他19岁的胡适,已更像一个老师。
1921年10月11日,吴虞作为新到北大的教授,在开学日做一次演说。主讲内容为“新文化再进一步之希望”。“意切实而语滑稽,掌声如雷。”他在日记里如此描述。除此之外,吴虞巨细靡遗的记录了胡适携其手一起进入礼堂的细节,连同事礼节性的拍手也不放过。他很看重他在北大的第一次亮相。但四年之后,他最“闪亮”的却是他嫖妓、为妓女做诗登报的故事。随着被北大解聘回川,吴虞和他所写的文章,迅速被人们遗忘。

四
冉云飞对吴虞产生兴趣,也是因为胡适给吴虞贴上的“老英雄”标签。但他后来失望的发现:“吴虞并不是学术中人,只是个知识的贩卖者而非生产者,是个教书的人而非真正意识上的研究者。他对历史的贡献,在于他非孔排儒的坚持与决绝,而不在于他说得有多么到位。”
随着对吴虞日记的反复阅读,冉云飞发现自己看到了一个病人。在《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》最后一章,冉云飞详细剖析了吴虞的心理状态:“长期压抑”、“背负道德的‘红字’”、“不安全感”,以及吴虞的认同危机和过度防卫。很自然的,冉云飞把这个病人和自己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,他在自序里写道:
“当我说吴虞是个病人的时候,并不是说我就是那个与病人对位的角色扮演者:医生。不,我承认自己是个狂妄的人,但在这件事情上,我不想如此狂妄,当然不是一位出色的医生。或许正是因为自己也是个病人——或许病的方式、角度可能与他不同——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他作为一位中国社会病人的痛苦。”
冉云飞时年44岁,其貌不扬,他自称“演座山雕不用化妆”。在生活里,他性情急躁,也可理解为豪爽。声音宏亮,常控制不住的哈哈大笑。朋友们戏称他是个山里走出来的土匪头子。但在博客里,冉云飞像换了一个人,他的思考和行文方式,让许多人以为他书生意气,羽扇纶巾。像胡适那样去思考问题。冉云飞最钦佩的人,也是胡适。
和吴虞一样,冉云飞也是四川政府的头痛对象。他对当地政治文化生态的批评,以及毫不掩饰的独立知识分子立场,无疑是许多人的眼中钉。但和20世纪初不同的是,成都的文化圈对冉云飞持开放态度,也从没有老百姓写信骂他。尽管冉云飞对“民意”持考察态度,但“民意”显然是支持他的。在成都,冉云飞能找到“英雄”的感觉──尽管他可能不太主动去找。
冉云飞并不是地道的成都人。1983年,他由重庆酉阳考入四川大学。他从小成绩甚好,但他认为中等教育是一个洗脑的过程。直到在川大中文系,冉云飞迎来人生第一个狂潮。他阅读大量的书籍,哲学、美学,参加各种社团活动。他从不和同年级的人讨论问题,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才是他学问上的伙伴。从那时起,他就是个刺头青,敢骂人,敢在课堂上让老师走人。四年本科,彻头彻尾改变了冉云飞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
毕业时,冉云飞有三个选择。一是去一个政府部门,但他自认为不适合当官;二是去一家报社,但他不想说假话,最终他选择了现在所工作的四川作协。起先,冉云飞以诗人身份在成都出场。他先后出过一些文学评论书籍,在圈内小有名气。1999年,他开始转型,出版一本批判中国教育的专著。这使他的名声逐渐超越了文学领域。
但此时“冉云飞”的名字,大多仍在四川省内知晓。只不过冉云飞并没有吴虞那种现实困境,他那时也乐于享受成都的生活。90年代晚期,覆盖全国的媒体并不多,而且大多是位于北京的体制内报刊。像大半个世纪前一样,北京依然有着不可抵挡的文化影响力。但随着市场化媒体的全国推广,报纸“时评专栏”的兴起,中国的舆论逐渐进入评论时代。在成都,冉云飞也在报纸上开专栏。可惜成都的报刊大多局限于西南一隅。
冉云飞也曾想过,是否要到北京去。但随之而来的互联网革命,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。在一篇论及互联网的文章中,他写道:
“在遇到互联网的同时,我重新遇到了胡适先生(以前读过胡适,但感受不深,所以叫重新遇到),遇到了威伯福斯等人,这是改变我精神历史的向导。同时,我遇到许多活生生的向善而做点滴努力的中国人,这许多的精神与现实事件合起来,逐渐造成了今天的我。我不是说今天的我有多么好,有多么了不起,而是说我在意自己艰难的变化。”
网络初起时,冉云混迹于天涯BBS论坛的关天茶舍。那时他依然是火爆脾气,常因为观点不同和人掐架,甚至与人谩骂到要与别人单挑打斗的地步。“重新遇到胡适”后,他对现实问题的思考,以及在网上的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。
在一篇名为《我希望这样思考问题》的文章中,冉云飞提及几个关键的思考方式:疑问;证据;论证;不比傻;宽容;认错。他说,“看清谎言的实质,并用中正平和、有趣幽默的文字,将其揭示出来,其快感是不言而喻的。”2005年,他开了博客。他认为博客经营得好,会变成一个比在BBS里更有影响力的个人媒体,变成关心你的人之精神食粮。
互联网让冉云飞暂时断掉了前往北京的想法。他博客的传播率已经覆盖到全国,并且延伸至海外。网络带来信息的多元化,对于人们看待事物,了解社会,培养思考问题的方式与能力,以及思维方式的变革,都有极大的影响。冉云飞说,“我一直说选择是自由之本,信息是民主之源,相信经过多年互联网的熏染,加上我们其他方面的努力,中国社会一定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变化。”
这种深刻的变化,自五四以来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期待。技术革命似乎正在带来其他方面的变革。吴虞终其一生所坚持的非孔非儒,在如今看来似乎已毫无价值。冉云飞说,他注定要被遗忘,因为他的思想无法超越时代。这个时代的主题,已经不再是激烈的割裂传统求得文化上的新生。但倡导民主和自由的胡适,却依然能再次启迪冉云飞。
2009年2月,我在成都约见冉云飞。那几天,刚好几个来自北京的时评作者齐聚一堂。冉云飞俨然一副地头蛇老大的形象。他几个电话就请来了成都的博客名人。有些人是第一次见面,却因为互看博客已久,并不觉生疏。冉云飞一一引见,饭局摆了两桌,他的声音响遍整个房间。在网络上,成都和北京,如今没有差别。
成都人乐于享受生活,在吴虞日记中,他也曾详细记录到过的饭馆和在座诸人。吴虞初到北京时,请吃不断,参加饭局者有许多知名人物。轮到吴虞所请时,均是北大的实力派。除了节前宴请,北大教员的迎来送往则是饭局诞生的另一个由头。1925年7月4日,吴虞意识到自己即将离开北大。他主动邀请一帮朋友聚会,其间北大同事,却已只有马叙伦和马幼渔──两个人。

五
离开北京,吴虞回到了他所熟悉的环境。但此时来自各方的压力已大不如前。北大教授的名声,使那些曾经的势利眼调转航向,吴虞此后在成都并未受到多大刁难。1932年春天,国立四川大学成立不久,第一任校长聘请他为教授,但一年后不知何故没有再续聘。
随着新文化运动接近尾声,新的革命又已到来,吴虞再也没跟上时代,他在后半生几乎一事无成。他偶尔看书,几乎不写文章。但他仍然在日记里记录一些《新青年》同人的踪迹。
陈独秀去世,吴虞在半个月后得知。在日记中,他像照抄新闻一样记录:“陈仲甫独秀,五月十七号夜半九时四十分逝世。安徽怀宁人,年六十四岁。寓江津,子松年。”他们因《新青年》结交,但终其一生,他们二人从未见过面。
1938年,吴虞花大洋1450元,在新繁镇北街购入房产,起名“爱智庐”。房屋是四合院布局,共有12间房,背靠东湖,环境清幽。在日记中,他称在新繁居住有七大好处。据说他厌倦城市的喧哗,对乡村的生活感到满意。虽然他一直在尝试纳妾,试图接续香火,但直到他1949年死去,也没有儿子。
五十年后,新繁镇旧城改造,牵涉到吴虞故居。政府宣称要进行整体搬迁。我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前往新繁,四处打听吴虞故居的位置,但所问十几个人,无人知道吴虞是谁。用蓝色铁皮围起来的街道改造项目,是一个大坑。施工人员拿着测量器具,规划着这个小镇繁荣的未来。
一个居委会的人告诉我,一直往郊区走,就能找到吴虞故居,在一个名为“吉祥原”的草原特色休闲度假村。随同吴虞故居一起过来的,还有一座大庙,祠堂,连同那条街上的“封建残余”一股脑儿,甩到了这片荒地上。它们的新老板是一个商人,向政府租用了这片土地。古色古香的旧房屋,在这个时代给成都人带来“怀旧感”的新鲜。
吴虞故居没有整体搬迁到此。只移来临街几间房。它们的门上分别写着“雅间1”、“雅间2”。屋子里已经很久没人落座,一张餐桌,一张自动麻将桌。在这栋孤零零的古建筑四周,簇拥着魔幻般的蒙古包。每个蒙古包内,都有一张餐桌,一张麻将桌。如同冉云飞所说,时代超越了吴虞。

所有图片来自视觉中国。
文章部分内容,取材于即将出版的《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》一书,在此向冉云飞一并致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