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我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中最少看过三遍《白鹿原》。
学校里有个湖南籍老师,姓单,在家排行老大,下面有四个弟弟妹妹。他一家三口住在学校分的一间不到20平的小房间里。有次我看他带着自己的宝贝儿子玩耍,手里托着个篮球瞄篮筐,小孩儿木楞楞地站着看。“单老师,”我叫了他一声,“你很喜欢篮球吗?”
单老师立刻把篮球抱在怀里,正色道:“我对一切体育运动都不感兴趣。”
不感兴趣就不感兴趣吧,可他把话说得好像早就看不惯什么事似的。我不交往什么老师,唯一熟悉的一个还这么愤世嫉俗,但我从他那里看到了很对我胃口的东西。他也带留学生,有一个学期结束时和我碰到,开口就抱怨说中国学生不如外国学生有修养。
“我班上的韩国学生,今天上我最后一节课,完课之后会上来跟我交流,拿一个小礼物出来表示感谢,”他讲,“我不是计较,我们这里的学生就没有这样的,他们想的是‘你是我雇来上课的’,合同一结束,我们各走各的。”
他教我们中国文化常识,而他的硕士专业方向则是中国近现代文学,也开了这门选修课。他说这是“一个学过之后就不想再学的专业”,因为“中国从民国到七十年代的文学就这么点东西”,学过之后,就知道这些人的思想和能力实在是不足挂齿。后来他把两大本《鲁迅书信集》都送我了,因为要搬家。
说着说着话就会慢慢把眼睛瞪圆,说到兴奋时就要抓两下头皮,单老师留给我的印象不出这些零碎的动作,愤世嫉俗的脾性则浸润其中。抱怨过学生之后,他就会讲起过去的学生不是这样的,过去的学生受着来自风俗的戒律,跟老师的关系,跟父母的关系,不是可以随随便便疏于维护的。
“那天我上课就跟学生说了,我说,你们去看看《白鹿原》,”他讲,“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人的道德感会败坏成这样的了……”
于是我知道了有一本书叫《白鹿原》,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堕落。我去买书,买到的是一个不多见的版本,淡绿色和淡紫色的压膜封面,没有任何反映小说内容或格调的图案,好像是一套什么文库里面的,文库么,规格整齐划一,不需要费心思设计。我开始读,读了几页就觉得单老师说得不对:传统中国已经很堕落了嘛,你看看白嘉轩克死这么多女人,你看看他阳具上的毒倒钩。
对比而言,今天的人开化多了。我宿舍里的其余七张床上都躺着比我大两岁的男人,可是看上去他们每个人都已是阅世高手。每个晚上熄灯后,在过道里咣当咣当地扔完酒瓶子,掀起报纸带走鸡骨头、螺蛳壳、泡沫饭盒、一次性筷子,他们一个个仰面躺回床上,例行地胡侃海吹,履行男人同志之谊里最坚固的法则:讲黄色笑话。他们大多数都有“马子”,所以,讲黄笑话不属于性爱冲动受挫后的安全阀,而是用来互相降火,消灭别人的热情。他们用上各种粗俗的词语、黑话,描述别人和自己的身体,他们刻意地把性爱吃下去又拉出来,变成一种荒诞,仿佛两性之间完全没有柔情蜜意。
我总要听完最后一个黄段子才慢慢睡着,心里还在嘀咕:“一群弱智,没看过《白鹿原》也好意思装流氓……”
他们邀我一起踢球,我也就去了,他们撇唇咧嘴的粗俗到了球场上似乎变得可接受了一些。我给他们当守门员,其实就是肉盾,扑不出几个球,支持我陪玩的武器是那句“我对一切体育运动都不感兴趣”。这是一种良心抵抗。《白鹿原》则变成了我同自己的一个秘密,虽然书就放在贴石灰墙的铁挡子上,但是人来人往,我从未被过问过。
当然,我也会把书跟自己的“马子”分享,人家的反应是“受不了你”。受不了受不了吧,谁没个适应的过程。那些没文化的流氓基本上没来招惹过我的私生活,但他们彼此之间却不乏出格之举。有一个晚上,上铺的三个男人突然跳下地,一起奔向我斜对面躺着的一个绰号“阿X”的哥们,一个坐在他的脸上放屁,另两个咯咯地笑着去拧他的肉体,“阿X”来不及团身,吭哧吭哧地笑着,蚊帐在四个男人之间绞成了一团乱麻。我立时想起黑娃拧鹿兆鹏裆下的那个片断。黑娃是受惯了鹿子霖摸裆后,在鹿兆鹏身上找点报复,但两人随即联手欺负起比自己小的白孝文:“孝文你,自个说实话,硬不硬?”
那是过去没文化的农村小孩做的事哎!中国学生确实很堕落。

▲ 电影《白鹿原》
等读到朱先生之死,书中特写了朱先生裆下那东西时我嘴巴都张大了,不明白陈忠实为何这么“忠实”。人跟土地的关系是可以、也应该用性来隐喻的,但那个时候我还不懂,只觉得朱先生很完美,很正直,我们不应该对一个正直的人的身体说三道四。小说的结尾也让我颤栗过一下:鹿子霖的尸体被发现时“刚穿上身的棉裤里屎尿结成黄蜡蜡的冰块”。一切不体面的细节小说都不避讳,不过既然鹿是一根老淫棍,算作报应也不错。
像“乡绅”“政治权威”“道德权威”这类术语,那时我并不太会用,但是写学年论文给了我一个机会。拿到系里印发的论文指导材料,我扫了一眼上面的四五十个题目就把它放到了一边,再也不看了,我觉得其中半数的题目都跟名词解释没什么分别。我自己写了一个题目交上去。系主任是一位在冠以“国际”之名的机构里有一席之地的专家,用我从卧室里学来的恶语,她长着一张“绝经脸”。她看到我的论文意向后,专门找了我一下,问我为什么如此乖张,不写本专业领域的题目。
我回答她:“你想看一篇东抄西抄的本专业论文呢,还是想看一篇认真写的非本专业论文?”
写出来有点挑衅,其实原话很婉转。其实我更想说的是“老师你开玩笑吧?我是一个读过《白鹿原》的人,我能写‘论XXXXXXX在国际海商实务中的应用与限制’吗?”
我骨子里的无厘头都被《白鹿原》刺激出来了。我去找单老师,我说,读完全书后有点懂他的意思了:白鹿原变成了一个你整我我整你的“鏊子”,而之前并不是这样的,之前虽然淫棍会去掏小孩的裆,女人会亮着胸脯奶孩子,但羞耻心是风俗的一部分。有朱先生在,就连布下的罂粟种子都能从地里刨出来,让白嘉轩羞愧难当,让“仁义白鹿村”远近驰名。虽然“仁义”二字并不属于现代,可是谁都看得出来,一个长幼尊卑有序的白鹿原要强过后来的动荡日子。
所以,我想就小说里白鹿村的乡规民约讨论讨论所谓“中国制度的本土资源”,谈谈今日法治还有多少传统的东西可以利用……说及这些的时候,我觉得我一下子进阶为“知识分子”,而非单纯的一个法律实务人员了。
单老师表示可以写。他教过的学生能有这种思考,不惜触犯了院系领导,对他也算一种不错的精神回报。我又问他,小说里的东西可以当真事那么来讨论吗?
单老师很难得说句不愤嫉的话:“那当然,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。”
我把《白鹿原》又完整地读了一遍。这次更多地关心到书中有关秩序和制度的东西。在秩序下面,白嘉轩和长工鹿三虽然是雇佣关系,其实如同兄弟,鹿三的儿子黑娃可以和鹿兆鹏、白孝文平等地玩耍。这让我想到十月革命后流亡的伊凡·布宁,他在《回忆录》中满怀怨恨地说,地主没有那么坏,地主也在辛苦赚钱,而阶级斗争思想的流毒把乡村秩序全都打破了;他永远不会原谅列宁。鹿子霖虽属无赖,可是秩序能够约束他的兽性。他读了朱先生手书的《乡约》都感慨不止:“要是咱们白鹿村村民照《乡约》做人行事,真成礼仪之邦了。”谁都看得出来秩序是种好东西。
这里面的理路和价值判断是很清楚的。《白鹿原》虽被誉为博大渊深,但人物归档简单清晰。博学的朱先生、徐先生并不是复杂的角色,远不像白嘉轩、鹿子霖那样必须活得世故玲珑。在乡村,有学问的人就有道德权威,能够教化一方,裁判世俗的争端;朱先生让白嘉轩把“耕读传家”四个字挖下来,白嘉轩立刻就慌了,于是罂粟田被捣毁,原上被鸦片败坏的风气一扫而空。
没人能否认它的合理。但所有的旧秩序都是在它夕阳西下的时候留下最好看的肖像,正像人总是在被追悼的时候得到最集中的表扬。朱先生很快被县里免职,罂粟花再次开放,表明“本土资源”是个多么空幻而无法长久倚赖的东西,只要权力不受约束。
但文学却是可以倚赖的。我轻车熟路地进入一个完全不熟悉的世界。论文提交后,我猜想它说服了一些老师,因为它被评为优秀。颁奖那天我因故没去,同学告诉我,系领导读出论文标题的时候引起了一阵骚动。那天晚上,两人世界的小小庆功后,我带着一张奖状,一个人若有所思地回到自己的床上,我的学长们正在调笑他们之中的一个,他一直空仓,刚刚接近找到一个“马子”。
他们快毕业了。我越来越频繁地闻到酒气。有两次,我晚上回来,被床上躺着的人吓了一跳,我使劲推推他,那人才慢悠悠地爬起来,走出去。很久没有听他们交流黄色笑话了,大概都在忙着找工作吧,工作是个多么无聊的话题,他们都懒得说,宁可把自己灌醉。一个共同体在瓦解,连我这么个局外人都感觉到了。
有一个凌晨,五点来钟,我睁开眼,见斜对面的上铺前站着个背影,好像是“阿X”(实在记不得X是什么字了),正在跟床上躺着的人说话。说话的声音有点怪异。起初我没在意,过了一会儿,我听出来他在哭。
男人的哭声很奇特,尤其一个一向满嘴下流话的人的哭声,那么不自然,好像把什么硬邦邦的东西给揉皱了似的。他一边抽噎一边说,掏着心窝子说,诉说他跟哥们的感情。我一下子想起了土匪黑娃抱着受辱的小娥的哭泣,想起了白孝文嫖妓挨打时的哭泣,想起了鹿三因儿子不肖的哭泣。《白鹿原》里有大把大把的男人泪,因为羞耻,因为仇恨,因为绝望。
个人生活里最重要的一部分,无法并入集体的那一部分,就是爱。但在个人的一段爱行将结束之前,他们似乎意识到了互相摸裆、互相淫人所爱的同志之谊的可珍可贵。他们说到了些什么,哭声渐渐扩大成了嚎啕,其他几张床上的人都凑了过来,讲出了我从没从他们嘴里听到过的话,满满的赤诚,各种粗鲁、尖刻、强蛮统统退散,取而代之的是有教养的温柔。
我想起白孝文、鹿兆鹏、黑娃这些白鹿原的第二代,分离之后就再也没能复合过。陈忠实写出了中国这个大“鏊子”如何拨弄他们的命运。鹿兆鹏和鹿兆海掷硬币决定该加入共产党还是国民党,只是戏剧性比较明显的一个桥段,人们必须先做出政治选择,然后才设法寻找依据证明自己是有理的,是对的。鹿兆海死于内战,白灵死于肃反,看不出作家更偏爱谁,但白孝文肯定是最令人不齿的一个,能在鏊子里活下来的,或多或少都是投机分子。

▲ 电影《白鹿原》
白孝文初夜闹窘,跟他存活到最后之间有什么联系吗?我看只是一种平衡,让更有男性气概的人死去,让小人苟安。黑娃爱小娥,而白孝文只是渴求小娥的肉体,结果黑娃死在白孝文手上。性本能偷偷预示着一个男人是否能活得坦然,但坦然却会让人付出生命的代价,重建起来的秩序,以孝文为代表,会继续凭道德之名封锁性欲……在没有人讲黄段子、没有男人荡笑的安静的夜里,我重新翻开《白鹿原》,补充生命中出现的巨大空白。
那是一本开满罂粟花的书,美丽而危险。我开始喜欢起里面的每一个人,包括那个猥猥琐琐,唱“小娥的奶,我想揣”的狗蛋。因为他们试过的毒是我的养料。我得庆幸没去学什么中文,在一群能把任何小说大卸八块的才子才女中间,我恐怕不得不去写篇关于海商实务的论文,那简直是比娶七房太太更加艰巨的任务。
我毕业的时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首先,恋情提前结束,其次我发现,因为长期缺少交流,除了说黄色笑话之外,我都想不出能跟男同学聊点什么,更要命的是,他们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听我讲完,然后呵呵两声,“听过了”,便散去。我没趣地离开,心里想着他们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,是不是也像那些流氓学长们一样,又拍大腿又敲墙,带着喉音狂笑一番。
《白鹿原》好像带走了我所有敢于和不敢表达的东西。当它成了一本很旧的书,打开它时,我听到很多男人的哭声从荷尔蒙的味道里钻出。虚构的哭,与现实的哭,混杂在一起,那些无所不用其极的粗俗与恶毒,那些暴力,不管出自哪个角色,好像都成了一种集体命运的一部分。男人互相攻击,互相讥笑,彼此嫉妒,甚至猥亵,在这个过程里结下可以抱头痛哭的友谊——我见证了它,却没这个福气分享。
佝着腰、垂垂老矣的白嘉轩,去看村里的公审大会,看白孝文主持审判并处死黑娃。“他背抄着双手走进会场,依然站在队伍后头,远远瞅见高台正中位置就坐的儿子孝文,忽然想起在那个大雪的早晨,发现慢坡地里白鹿精灵的情景。”然后,他挤到前面去看死刑犯黑娃,见黑娃“掉下了清亮亮的泪珠……”现在,再读书中这个心爱的段落,我会想起茨维塔耶娃《约会》里的句子:“我赋予我的爱给你,它太高了/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。”它宽容地启发我说,所有交往,管它是相爱还是相杀,都是——约会。那么,这对占有过同一个女人的黑白冤家,在小说塑造的现实里搏杀一场后,幽灵或也能在未来重聚……我真心希望是这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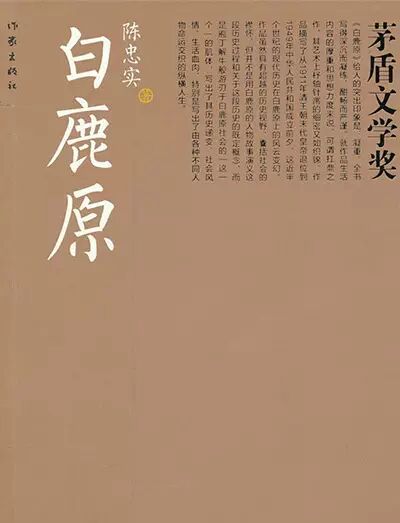
▲ 作家陈忠实代表作《白鹿原》
(本文原标题为《我引以为豪壮的是看过三遍〈白鹿原〉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