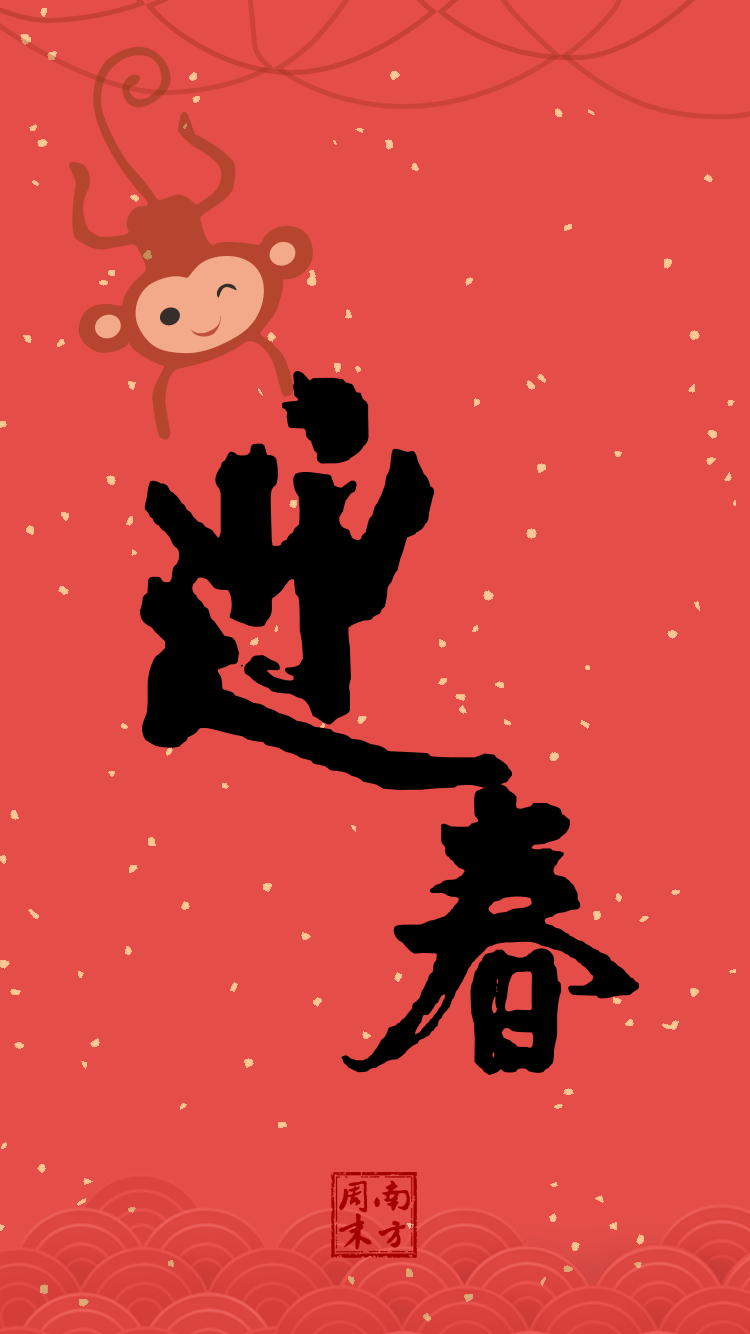除夕这一天,除了家庭身份,中国人的其他社会身份暂时失效。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,都回到自己最亲近的血缘关系人身边,都回到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。从大年初一开始,社会化的关系开始呈现。这样的设置,像一个重启键,把所有不幸和不满归零后重启。
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
微信号:nanfangzhoumo
除夕是“我”的,春节是“我们”的。在很多人眼里,除夕和春节就是一个节日。尽管它们有两个名称,前后连贯,但都可以统一到“过年”这个概念来。可是在我看来,除夕和春节具有本质的不同,一个属于“家”,一个属于“社会”(本文选择社会的狭义定义,特指社会的非家庭属性)。
除夕这一天,除了家庭身份,中国人的其他社会身份暂时失效。你不再是老板、员工或学生,而是父亲、孩子或妻子。你可以在任意一个节日进行社会化的聚会,比如中秋同学会、端午老乡会、元旦战友会……甚至在大年初一,你都可以呼朋唤友去打牌。可是,除了不能回家的人以外,你发一个除夕朋友聚会帖试一试?
闽南人把除夕叫做围炉,指的是一家人围在一起。这个家,特指最近的血缘关系。哪怕在姑姑家过除夕,仍然有在别人家过年的感觉。到了初一,就可以按照远近亲疏,开始对外拜年。我老家湖南流行一句:“初一崽、初二郎”,初一是分家过的儿子回来拜年,初二是女儿和女婿回来拜年。即便是最疼的外婆,也排不到除夕这一天。
从大年初一开始,社会化的关系开始呈现。有的领导或老师,很在乎部下或学生是不是第一个向他拜年。上下级、师生,这些在除夕退隐的社会关系,到了初一,就都重现江湖了。现在流行微信拜年,其实待在你身边的才是你的至亲,而微信拜年的通常是你的社会关系。
初一过后,社会关系逐渐展开,直到元宵,从熟人社会完全进入陌生人社会。元宵晚上,不仅待在家里是“可耻的”,甚至待在别人家里也不行,有屋顶的东西都不属于元宵!元宵灯会,在遥远的过去,这是女孩子名正言顺可以大面积地见到陌生男人的不多机会。在有关元宵的古代诗词里,陌生男女青春期的躁动溢于言表,真的是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”。其实看灯是假,看人是真。不丢一个手绢、捡一个手帕,算是白白过了一个元宵。
元宵过后,人的社会关系进一步扩大。从家乡的地域扩大到整个世界。打工的出外打工,上学的回校上学。没过元宵就外出,是家人永远的遗憾。我父亲年轻时有一次没过元宵就被迫外出做生意,那一个雪地的出行,令他在回忆录里仍耿耿于怀。
这样的节日设计,每年都对家庭和社会关系进行一次巨大的调控。除夕之前,像一个>(大于号),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到除夕全部趋零,只剩下家庭关系;而到了春节之后,像<(小于号),各种社会关系依次恢复。除夕和春节,不仅调控社会关系,而且改变空间关系。在除夕这一天,你唯一的位置,就是待在家里。所以,天南海北,也要赶回去过年。而从春节开始,人们的物理空间又开始慢慢从家里出发,直到越走越远。
这就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人口大迁徙。它带来了一些社会难题,比如春运。那一年的大雪,有经济学家呼吁:中国人应该改变除夕回家这个“陋习”,有关部门要培养人们就地过年的“新风尚”,这样可以大幅度节约经济开支和社会成本。
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的负担,在历史学家眼里可能恰恰是财富。世界上的几大文明之源,最后都断流,惟独中国有一个不曾中断的文明发展史。中国也有暴君瘟疫,也有外族统治,但所有的外力,都毁不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。这个生命力的存续也许和中国的节庆设置不无关系。如果每一年,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,都回到自己最亲近的血缘关系人身边,都回到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,这样一个回到源头并重新出发的全民族活动,年复一年、无一例外地进行,你想中断这个民族的历史谈何容易?
除夕和春节这样的设置,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复原工程。它像一个重启键,把所有不幸和不满归零后重启系统。中国人碰到不好的一年,都祈望它早早过去,“新年好”不仅仅是简单的问候语,也是中国最大和最了不起的心理医生。无论人们在外面受过多少委屈,到了除夕的家里,就会发现你是大家最挂记的那个人,而最记挂你的人就等着和你在一起。“文革”中不少自杀的人,不是毁在红卫兵手里,而是毁在被批斗回家的最后幻灭,因为在家里还要面对与自己划清界限的“革命”亲人。对家庭的破坏,是对个人和国家最残酷的伤害。理解这个道理,就可以明白除夕和春节的设置,多么值得我们点赞!
我的除夕和我们的春节,脉动的是中华民族的舒张压与扩张压,它让每一个人的静脉血回到心脏,又重新输出充满活力的动脉血。再强大的力量都改不了这一个血脉的正常跳动,因为不断重启,所以生生不息!
在又一个辞旧迎新的佳节之际,恭祝每一个接受民族文化精神洗礼的中国人,无论“我们”的世界多么混沌,都可以找到“我”的归宿和出发点。让我的除夕,温暖我们的春节!
(作者为厦门大学教授)